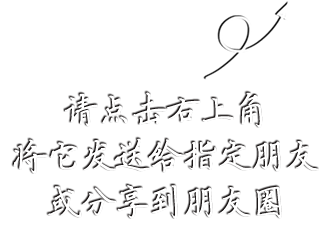中国正在进入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协调阶段,中国产业大迁移并没有发生在传统产业,而是发生在新兴产业。
过去三年,一线城市高房价对制造业持续挤出,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聚集。
目前北上广深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已突破60%,中国一线城市的最终产业发展形态可能类似于纽约和东京,成为一个服务型和消费型社会。中高端制造业(半导体、通信设备、电子元件中国吊车网)向地理纵深发展,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迁移的特征。产业迁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崛起,形成以新兴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。
新兴制造的迁移方向和地方政策、工业基础、区位优势的匹配度高度相关,例如合肥的中科系、武汉的光谷系、郑州的富士康系、以及成都西安的科研和半导体产业等。
合肥重点扶持芯片、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核心基础产业,以及软吊车出租件、5G等核心信息技术。
武汉重点扶持光纤通信产业,东湖高新区(“中国光谷”)是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。
郑州围绕着富士康作配套,搭建电子制造的产业链集群,建设五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。
西安将吊车维修半导体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,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。
贵阳重点扶持电子元件产业,大力推动与英特尔、戴尔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。
中国正在进入区域发展再平衡、产业布局优化、产业链集聚的新阶段,这也是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彼此协调的过程。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把旧产业从东转到西,实际上旧产业并没有转移,只是在出清过程中向高效率低成本地区集聚。真正发生了产业迁移的是新兴产业里的中高端制造,这也是各地再创业的过程。
产业迁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,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产业迁移的必要因素。基础设施、工业基础、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资源禀赋更加重要,一旦时机配合,产业布局的再平衡就会出现。中国产业大迁移,始于制造业,必然带来劳动力、资本、税收、基建等方方面面的变化,进而对人口流动、房价、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。70年代美国开始从北到南的产业大迁移后,美国的新兴制造业、消费零售和服务业在80年代前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。
随着中国新兴产业持续向地理纵深发展,未来十年的中国在消费、服务、中高端制造上的潜力不可估量。